原生于澳洲的桃金娘科桉属植物(eucalyptus),音译为尤加利,是近900多个亚种、变种的总称。广为人知的桉树包括蓝桉、赤桉、细叶桉、大叶桉等, 最先是作为观赏植物由意大利公使于1890年引入晚清宫廷, 后因“生长迅速、干材挺直,材质坚硬、利用价值宏大”逐渐扩种到接近原种生境的广州(1890年)、福州(1894年)、昆明(1896年)、西昌(1910年)、合浦(1920年)等南方地区,与另外两种更有气候普适性的优良行道树种(美国洋槐和英国悬铃木)构成晚清民初中国城市植景“异域”情调——北平五月槐荫绿海、沪上租界梧桐大道、昆明海埂桉堤……见证晚清以降,卷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如何在风景层面一步步全球化自己的都市植被(vegetation cover),确言之,外观。
作为世界三大最优速生树种之一,桉树的用途范围和经济价值远超杨、松,备受中国政治家、经济决策者以及林农学家的青睐。经由晚清外交家吴宗濂(1856-1933)引介、广东军阀陈济棠(1890-1954)倡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委员长(1886-1976)等人力推,加上侯宽昭、祁述雄、谢耀坚等几代(桉)林学家努力,桉树渐由观赏植物、道路绿化树跃升为中国现代林业的主力树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基本国策、木材和纸浆巨大需求及延伸利益的驱动下,中国桉林、桉园、防风桉林带等不断扩大,高速发展,到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种植面积已达440万公顷,分布于大陆19个省600多个县市,超过印度,仅次于巴西。经过120年的引种、归化和推广,原为澳洲本土植物的桉树重塑了中国南方诸省甚至一些北方地区(如陕西汉中)的植物群落,在提升乡村经济水平,造福于国计民生的同时,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埋下将要激发公众焦虑的环境难题。
自然地,一如公元前二世纪张骞等引入汉土的伊朗苜蓿和葡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转给我们的美洲作物烟草、玉米、甘薯,土豆,澳桉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的巨大存在,并入植物交换引动的文化汇(transculturation),嵌入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潜入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想象——沈从文、林徽因、冯至、于坚、李浔等人笔下的尤加利或桉树书写佐证:一个群体从另外一个群体引入一种事物或植物,“人们会通过适应、改造记忆混合的方式让其本地化,从而适应自己的需求和境况”, 进而内化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近二十年来,澳桉引发的争议和舆情却是那些自汉朝以来源源不断输入中国的外来植物所未遭遇过的。部分拜密集、交互、广泛的新媒体传播方式所赐,围绕挺桉、限桉、禁桉、复种所展开的多方博弈和争议逸出林业、经济、环保范畴,演进为公共话题甚至激推出社会事件,由此引发的公众口述、描述、评论、权威部门的政策背书、利益方的专业修辞或广告、生态学家的数据、环保主义者的抗议等与相对超然的文学书写构成了一种“复调”话语现象,各个声部互相搏斗、追逐、缠绕、分异、汇聚,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受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基于物种(植物)大交换的全球环境史和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以植物为中心的跨学科批评(critical plant studies)启发,结合近年风景类型研究的新进展,笔者开始关注被誉为“造林嘉木”“未来之树”“绿色黄金”“奇迹树”的澳桉如何逐渐取代中国乡土树种,撑起1/4的中国森林工业;观察不断扩散北移的人造桉林如何消减东南沿海、西南山区、中南丘陵不同地区原生植物群落,将西方曾经垂涎的植物多样性天堂,从云南楚雄到广西十万大山再到四川金沙江河谷同质化(homogenize)为单调高产的全球性林业景观;追踪澳桉如何被各种传媒拽进公共话语空间,渐渐被描述为“抽水机”“吸肥器”“霸王树”“灾难树”“亡国树”……,在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同时,又引发桉树学家集体性“焦虑”:后者担心媒体与公众共谋的“社会偏见”将会危及中国的木材安全;思考中国文学家对外来桉树的想象与澳大利亚的本土桉树崇拜是否有共通之处?抑或大相径庭?各自的想象和表述在一部全球视野的桉树文化史里具有何种意义?……在有限篇幅里,本文暂且锁定四个方面:爬梳澳桉引种史料和劝种话语,综述当代媒体的倾向性观点,分析公众对于单一桉林的感知,比较抗战期间旅居云南的学者和作家的桉树书写,试图呈现晚清以来中国如何接轨世界造林体系来应对自己的环境难题;如何因单一的桉树种植而卷入全球性生态同质世和文化后效之中;以及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桉树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甚至文学想象。
一
全球化诞生于哥伦布大交换。大交换时代,欧洲博物学家,或者说,植物猎人成为时代英雄:他们勘察那些所谓未知或处女疆域,“发现”欧洲感到陌生和不曾拥有的植物——从贵重的经济植物(如豆蔻、橡胶)到药用植物(如大黄、金鸡纳霜)再到观赏花卉(如热带兰花、云南高山杜鹃),甄别和命名植物属种、功用、价值等,确定它们与欧洲的归属关系(通过引种、归化、培育新品种、建立海外种植园等)——这种植物学的帝国野心源自并成就了克罗斯比称之的“生态扩张主义”。
英国邱(Kew)植物园的创始人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是英雄的英雄。1770年,他跟随库克船长“奋进号”首航太平洋,在澳大利亚植物湾一带收集到大量标本,包括他称之为黏胶树(gum tree)的桉树,后来被法国植物学家德•布吕泰勒(L'Héritier de Brutelle 1746-1800)根据其隔膜包裹花蕾(cap covers bud)的形态命名为eucalyptus。
班克斯是一位精明而有远见的贵族植物学家,毕生致力于将异域植物转化和开发成帝国可获暴利的经济作物,例如,“将南太平洋的面包果树引入西印度群岛,将茶从中国引入印度。”然而,他并未预见桉树将作为澳洲唯一回馈旧世界的物种,会“全球化”世界林业体系及关联经济,更不会前瞻这次“乍然相逢”的生态后效:自19世纪初开始,桉树凭借其生物优势,远播、扩散,用生态学术语来说,“大规模入侵”120多个国家,包括距离澳洲万里之遥的晚清中国。


当速生易栽的桉树郁蓊于一度沦为“秃赭山地”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成为意、法、西、葡诸国“食利不已”的新富源,曾经排名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大清正临近崩溃:内外交困、国弱民贫,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尽管政治制度本身已经积重难返,但一批有识之士依然对实业救国充满幻想——如果说,16世纪中期经由东南亚传入的美洲农作物引发了中国“粮食生产的革命”,帮助入关不久的清政府迅速巩固了远离传统麦稻产区的地方统治,那么,帝国末年,从洋务运动的领袖(如张之洞)到戊戌变法的中坚(如康有为),甚至力挺祖制的遗老(如罗振玉)则寄希望于“广兴艺植”,重振中国林业,进而达成富国裕民的目的。这一时期,时有“振兴林业策”(罗振玉,1900年)“论林业”(佚名,1904)“林业宜推广说”(佚名,1904)“论我国急宜振兴林业”(佚名,1907年)之类的建言见于《农学报》《商务报》《广益丛报》《牖报》等,主旨不外“林业亦为生利之大端”、“富民之政虽多,非先振兴林业不可”等等。1906年,御史赵炳麟上奏光绪皇帝:
近日英、美日本列邦,其所以图富强者,事不一端,而尤以农林为先务。盖农林者工商之母,财富之源,故必设专学以研究之,立良法以维持之,使国无旷土,野无游民,悉合我国古时王政也。中国农林废弛久矣,……皇上念本图,重民食,特立农工商部,意在举孟子所述王政,见之实行,且参用东西各国新法新理,我国转贫为富,化弱为强,此其关键。
赵氏颇能代表晚清民初知识阶层的“时代情绪”:焦虑和乐观。焦虑于林政不修所带来的环境危机:森林资源枯竭,民生凋敝;乐观于造林十年即可获利,国运回春的前景。这种情绪甚至感染到负笈美国深造林学的陈焕镛(1890-1971)。1911年1月,他在《中国留学生月报》发表“中国林业”一文,将中国林业的兴衰与文明的存续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所面临的林业困境都不及中国的巨大。在危及她的繁荣、未来及生命的各种事务之中,林业困境最为紧迫也最具破坏性。然我国讲求林业者寥寥无几。造林不容耽误,毕竟焕然改变濯濯不是一日之功。”在此语境之下,有识之士逐渐达成“振兴林业、选种为先”(梁希语)的共识。他们一方面向外广求“繁殖易、生长速、用途广”的经济树种,如美国刺槐、楸树、英国梧桐、巴西橡胶等,一方面向国内民众推介良种的性质、用途及栽培方法, 冠名“劝种洋槐”“劝种梧桐浅说”“劝种杨树浅说”之类的科普文章风行一时,而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引种桉树的专著,吴宗濂辑译的《桉谱》由商务印书馆代印,附录的桉树照片首刊于1910年的《东方杂志》,并以“劝种桉树”的标题重刊于《广东劝业报》(1910年)和《安徽实业杂志》(1919)。吴氏盛赞桉树是“嘉木珍品……树之十年高可参天,性质坚韧,与椐木相类,取材甚广,大者可备栋梁之选,小者堪应器具之需,利物卫生,与国脉民生大有裨益,……”。
从1910年到1947年, 继《桉谱》之后跟进的20余篇推广桉树的文章,两部设有桉树专节的论著《造林学各论》及《科学知识》),虽然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桉树“皆有莫大之利益”,不仅关乎我国林业前途,甚至民族存亡,如袁汉邦的《种桉树为吾粤林业之先务》(1922年)和戴渊的《湘省倡造桉树林芻议》(1943)等,特别是后一篇,写作于中国抗战进入僵持阶段。作者有感于大后方的铁道交通建设木材短缺的现状,而桉树七八年即可成材,建议:“际此抗战时期,吾林界之育苗造林,宜以采植具有国防经济价值,而又能适合当地风土之特用树种为目标。故于湘省倡造桉树林,但有其迫切之需要在焉。”显然,这篇芻议的价值已经超过林学范畴,其所透露出的务实态度与乐观精神成为一代林人的写照:坚信中国一定能够赢得胜利,并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细读劝种桉树的话语以及相关“软文”,我们发现:限于晚清民国的历史条件,最初作为庭院观赏树和行道树引入的澳桉并未得到大面积推广,取得吴氏展望的“倍蓰之利”,但其蕴藏的巨大价值还是逐渐得到民众的关注,并与剧变时期的诸多中国经济文化议题密切交织。
二
澳桉的“生态扩张”始于19世纪初,但直到20世纪下半期才进入高速甚至失控的发展状态。随着世界范围的人口剧增、原始森林剧减,许多国家不得不选择集约高产的人造纯林来解决日趋严重的“木材危机”。桉树成为造林首选,并被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列为战略树种。对于澳桉的全球扩张路线、范围、功用,地理与环境教授Robin W. Doughty 在其开拓性专著《尤加利:黏胶树的自然商业史》(The Eucalyptus: A Natural and 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Gum Tree)做了清晰而有画面感的勾勒:“当今,桉属到处发荣滋蔓,马赛克一般镶入新旧世界环境之中(a mosaic of environments),从海平面到海拔一千米的高山。桉树种植园,桉树森林、桉树林地、桉树墙篱、城市街区林荫大道占据了数以千万公顷的土地。桉树固定海岸和运河堤坝,美化庄园、公园、游乐园,屏护农田和果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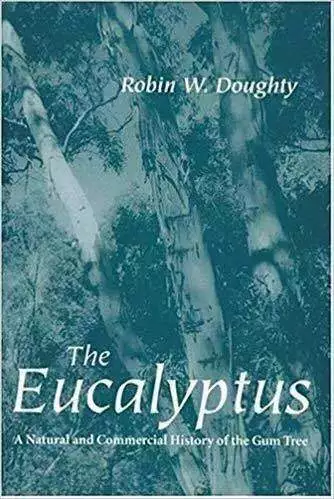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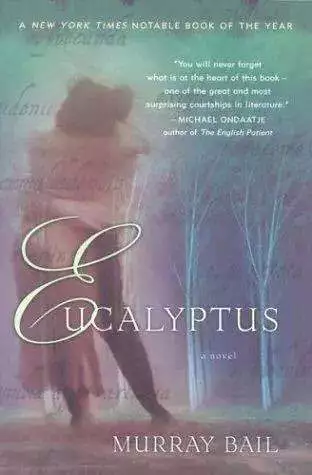
这幅大到1000多万公顷的环境马赛克包括中国460多万公顷,分别由(不完全统计的)广西3000万亩,广东1650万亩,云南400万亩,福建350万亩等构成。
如果数字是抽象的,那么媒体的描述、图像、民众的口述,自媒的表达等也许能将数据“可视化”为浩大的暗绿林景,单一的桉树海洋:
“十一五”期末,广西桉树面积发展到2480万亩,占全区人工商品林面积30.5%,相当于每个广西人拥有半亩桉树。
10日上午,记者沿水官高速出关,高速路两边时而可见成片桉树林,灰绿色树叶成片、分布成型,与周边树木形成强烈对比。桉树枝叶主要集中在树顶,如帽子状,下面是光秃秃的树干,呈现白黄色。一棵20米高的桉树,树帽长占四五米,树干达到十五六米。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高明、三水等地,原产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在佛山正“疯狂”生长。林业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佛山桉树纯林种植面积已占到全市林业用地面积的四成。

……
细读纸媒和互联网相关描述,就会发现: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曾被吴宗濂视为“利物卫生,与国脉民生大有裨益”澳桉经过提速推广和大规模扩张之后,不可避免地演入全球环境史经典而反讽的剧情:
番薯,和另一种美洲迁入物种玉米一样,的确帮助中国走出了灾荒。但是它们也引发了另一次灾难。传统的中国农业主要关注水稻,这种作物必须在湿润的河谷地带才能生长。番薯和玉米可以在中国干旱的高地上生长。成群结队的农民走出去,砍掉了这些高地上的森林。结果就是灾难性的水土流失。淤泥填塞了长江和黄河,引发了导致数以百万人丧生的大洪水。
在那些早于中国大规模植桉的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加州、葡萄牙、印度等,相似的剧情已在20世纪70、80年代屡屡上演,引发普遍的生态警觉和频繁的抗议,当然也催迫出桉林专家的密集辩护。在中国,类似的生态焦虑延迟发作,80、90年代,相关争议主要在专业范围内进行。 但是,2009年始于云南的南方大旱使得澳桉高频聚光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高清照片显示在“亚洲水塔”的云南,大江滞流,河溪干涸,池塘见底。一般公众认为连年大旱与失控发展的桉树林业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的观点或见于著名媒体的采访报道,或缓存、隐匿于一些网站的讨论区:
我是云南人,大旱让人们揪心!树这几年真的砍多了(成片成片地砍光了保水固土的原生的灌木林,来种植单一的思茅松,桉树,橡胶树及茶树,使得土地板结,土壤保水性很差!)
近几年来,我们家乡大量种植桉树,虽然经济收入客观,造福农民,可是年复一年,水资源枯竭的很严重。以我的亲身体验为例,我们寨子十年前还没有人种植桉树,现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把土地种满桉树,原本郁郁葱葱的森林现在被破坏的不成样子。
类似这样“事实描述”不胜枚举,而桉树专家一律将其归类为社会误解、媒体误导和民间传言的“桉树X宗罪”。总体而言,大众新媒体的叙述和观点,倾向于支持禁桉的生态学家和社会学家,而挺桉专家不断发表桉树耗水、耗肥、木材产能,扶贫效益等试验数据、图表和分析,认为桉区频发干旱、水土污染等应归咎全球厄尔尼若现象和林农不科学的密植,施肥、喷药、砍伐等,试图扳回妖魔化桉树的倾向。
显然,在凭借直觉和观察的“民间说法”与依靠试验和数据的“科学解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困扰决策部门的取舍(种还是不种?禁还是不禁?),但也凸显了当代人的生态焦虑或意识,因而具有重要的环境史学价值。很难想象,在古典时代、前现代时期,甚至20世纪60年代,一种外来经济植物会在中国搅动如此普遍的反应,激发这么多的学术非学术争论,许多经验描述、情绪表达和环保诉求来自依赖桉树经济的草根阶层。比较之下,苜蓿,甘薯、橡胶树等几乎是以“不知不觉的”方式参与塑造中国环境和历史,而大众对它们的环境后效及文化效应则是后知后觉,甚至无知无觉。
桉树生态争议持续有年,迄今没有平息——这一现象也许颠覆了一个世纪以前美籍藏学家劳费尔(1874-1934)的一个结论: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体系,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在植物经济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中国有一独特之处:宇宙间一切有用的,在那里都有栽培。当然这些植物的采纳和吸收的过程是一步步进行的。
颠覆旧结论的力量部分来自哥伦布大交换及后续势能。套用克罗斯比的话来说,中国南方广大地域的生态系统,已因澳洲桉树的到来和繁衍完全改观,通过多种媒体的跟进、聚焦和放大,“裸呈”于公众面前。因此,也可推论,颠覆旧结论的力量部分还来自媒体,再次证明生态焦虑,或者说,生态争议也是一种全球化症候。一如那些捣毁桉圃的泰国农民,要求禁桉的巴西种植园农工,清除公园桉树林的美国加州市民,对于澳桉,我们同样经历了“好奇、容受、讥诮、怀疑、敌视”, 不同程度地卷入争议之中。
在挺桉派看来,生态学家、环保主义者、民众关于桉树的很多负面描述属于片面、非理性表达,经不起科学数据的反驳。对此,世界农用林业中心首席科学家,昆明植物园研究员许建初博士提出相反的看法:“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外来树种(exotic tree species), 那里原来本来覆盖着多年生青草,它们蔓延的根系是地表土更好的保护者,单一种植(plantation monocultures)几乎无法涵养多样性,庇护本土濒危的森林物种。”

他的看法契合环境史学家曼恩在全球范围(包括云南西双版纳)展开的田野考察。基于单一树种经济林,无论是桉树林,还是橡胶树林,是“最宁静的森林”,“没有鸟也没有昆虫”,因为它们都必须依靠高效肥料和杀虫剂降低劳动力成本,控制争夺水、肥和阳光的“无用的杂草”——而这后两样造成了蕾切尔.卡逊笔下“寂静的春天”:“然而当灭草剂降落在森林和田野,降落在沼泽和牧场的时候,它们给野生动物栖息地带来了显著的变化,甚至是永久性的毁灭。”
三
即使最坚定的挺桉派,中国桉树产业技术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谢耀坚教授也提到单一澳桉纯林的缺陷:“与其他的人工林一样,桉树人工林是一种人类直接干预和创造的森林生态系统,……其物种多样性、生态稳定性差一些,总体生态功能弱一些。”然而,“差一些”、“弱一些”已经说明集约化纯林(plantation)与传统意义的原生森林(old-growth forest)本质区别:人工生态体系的同质性与自然有机体的多样性——前一种看起来像是森林,“但是生态学家可能不会这样称呼它”,后一种意味着乔木、灌木、藤、草参差百态,走兽、飞鸟、昆虫物竞自由的“林景”:文明从其诞生,诗歌从其萌发,哲学受其庇荫。
因此,原生森林不仅关乎一地一国之民的生活资料(食物、燃料、建筑用材、药物等),而且作用于集体意识、民族性格、文化认同等塑造。也因此,从东方到西方,一国特有树种,特别林地,特指林区往往被列入“国家文物”,而其他国家也将其视作是它的文化渊薮和民族象征。这一方面的史料和分析,在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中第一部分“木(Wood)”俯拾即是。例如,在德国,自中世纪以降,橡树神话、橡林崇拜和黑森林浪漫化就和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盘根错节为迷人而危险的民族植物史:“……德国的森林不只是一种经济资源,在某种神秘、不可确知的方面,它们就是“德国之所以是德国的东西。”
毫不奇怪,面对森林,哪怕是标明“木材储备,纸浆来源”的商业桉林,许多人会情不自禁进入审美状态,超越经济价值的计算(比如树龄5年的桉树每亩可得多少政府补贴,收入多少)。悖谬的是:在如此倚重人造桉林的中国,目前为止,近千篇关联论文中只有几篇稍稍涉及桉林的景观价值和美学维度,由此可见,在当代很多林业学者思考体系里,林业与美学处于隔离甚至对立状态,以至于个别学者怀疑倒桉言论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审美效果”。
终于有人提到了桉树“审美”价值,尽管是以质疑的态度。悖谬再次出现:被当做观赏植物引入中国的澳桉随其经济价值上扬,面积激增,逐渐成为大煞本土风景的杀手。
广西桉树面积居全国第一,业内素有“世界桉树看中国,中国桉树看广西”之说,因而桉林环境后效在广西最为明显,生态论战多方都会采用广西案例,如中国林学会2016年发表的《桉树科学发展问题调研报告》。爬梳散见于广西地方贴吧、论坛和个人公号等关联话题,笔者发现:在依赖桉树经济的林农或村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已超越政策因素和经济盈亏的考量,不仅具有清晰定位的环保诉求,还有一定的美学感知:他们回忆童年与森林的密切关系,对林景四季变化的细微感知,流露出失去原生林的感伤:
“从前我们周围的山上全是原生竹林,松树林,松树普遍直径都有一米左右。山清水秀的。一年四季山里的溪流从未断过水,山上的小路都是湿漉漉的冒着水,随便看到的小洞都能抠出小螃蟹来。六七年前政府把山包外地人后,把山上的树全砍光了,看着一车车那树干两个人都抱不过来的树被砍掉运走不知道多心痛,树砍完了一把火烧山后全种了桉树。到现在溪水断流了,村前美丽的河也干涸了。……”

“……广西自从大面积种植桉树,在桉树种植区,古树、清泉、山花、野果等森林带给人们的人文情怀已经被彻底消灭,即使现在开始全面铲除桉树,有数代人也只能通过书本和影视作品了解森林的作用和美丽。
……
也有逆向而行的个案。容县寻阳村拒绝炼山种桉:“把一个个山头的树木砍个精光,然后开发种植速生桉”,坚持不懈保护自己的乡土古树:榕、楠、松、格木、橄榄树等,“使这里的山林从未受到所谓的开发和毁坏,一年四季苍翠欲滴,……成为容县保护得最好的原生态林区和令人向往的乡村生态游景点。”
匿名网民的感受和寻阳村民的自发行为典型地呼应了历史上一次次“乡土植物VS外来植物”的美学战争。每当外来树种压倒乡土树种,哪怕它已完全适应移入地的气候和土壤,嵌入本地环境之中,依然会引起当地人的美学不适和感情疏离。例如,19世纪末期,为了重新绿化滥伐森林遗留的童山秃坡,英国林业部门在湖区、苏格兰高地大量引种速生耐寒的日本落叶松(Japaness larch),急剧甚至不可逆地改变了这一区域的地景。当全球游客朝圣“一生必去之地”,如画的英国湖区时,几乎无人能识别由暗绿的针叶松林、青翠的牧场、绚丽的杜鹃灌木丛构成的英伦乡村风景中的东方元素, 当地人和环保人士则认为落叶松弱化了湖区特有的英国气质,“破坏了神圣的国家遗产”,遂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保卫英格兰树(Save England’s Trees)”组织,发起一系列恢复本土阔叶树的请愿活动。
无独有偶,美国澳桉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部分民众也曾动议清除澳桉。19世纪中期,加州人引种澳按的动机与吴宗濂《桉谱》所宣传的如出一辙:解决木荒,提供燃料,降低疟疾等。因高度适应当地生境,1927年,“入籍”半个世纪的澳桉被《洛杉矶时报》宣布为“比许多本土树种更能代表加州”。即使如此,本土树种热爱者认为澳桉的“入侵性(invasiveness)”抑制其他本地树种的发展,遮蔽了本地植被原貌。
这里,再次出现一个悖谬:19世纪美国的西进开发,包括加州淘金热与大规模滥伐加州原始森林相伴相生。及至19世纪中期,当澳洲农民坐着蓝桉甲板的船只来加州拓垦,他们发现:憧憬的应许之地已经变成无树的荒凉(bleak)之州,仅在少许砍伐不便的山地还残留一点本土的橡、柳、月桂树丛。自然而逻辑地,速生易栽的澳桉很快遍植荒山海滨,最终演进为加州主导性林景。1904年,美国农林学家Alfred McClatchie((1861–1906) 写道:“没有尤加利,加州会完全不一样。一旦把它们从加州抹掉,市民就会明白它们存在的意义。没有它们(正是它们使得风景多变柔和起来),加州风景一定显得单调和乏味(monotonous and unattractive)……”

百年之后,随着澳桉人工林生态弊端渐渐显露,加州人的感知也发生了分化。对部分加州人来说,澳桉犹如新写在旧羊皮纸卷上的故事,擦写替换了记忆深处的本土红杉、橡树、杨柳等;但在澳洲移民眼里,高耸(lofty)而庄严的(majestic)尤加利使故乡“栩栩可见”,童年歌谣“桉树上的笑翠鸟kookaburra in the gum tree”隐约可闻,慰藉他们的乡愁。澳桉与澳大利亚乡愁的同构关系在两部著名的澳大利亚小说《荆棘鸟》和《桉树》(Eucalyptus)有生动的体现。
同一片土地上的澳桉引发截然不同的感知,就像一个错综无解的悖谬:“这些桉树很美,味道好闻,它们是猛禽栖息地,能够防止滑坡,但就是有些人,因为审美理由(for aesthetic reasons)不喜欢桉树。”默里﹒鲍尔在其小说《桉树》里一段议论也许更能生动地解释这种“不喜欢(dislike)”:“太多的澳桉输出到世界各地,长大成材,挺拔醒目,污染了当地风景的“纯粹(purity)”。一眼望去,意大利、葡萄牙、印度北方、加州的夏景与经典的澳大利亚风景毫无二致。再细细一看,就能感觉它们的“格格不入(out of place)”, 仿佛在苏格兰或塔斯马尼亚看见长颈鹿。”
无解的悖谬同样困扰昆明。2012年,生态争议达到峰值,五华区砍掉一百多棵澳桉和澳洲银桦,“配合着目前正在进行的翠湖环路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替代逝去桉树、银桦树的将是滇朴、栾树、喜树、桂花、山茶、樱花等本地树种。”这一行动引出的网友热议与一些桉农和生态学者的反应南辕北辙,启人思考:谁的桉树,谁的记忆?谁的美感?
四
在《树、林及森林:一部社会文化史》(Trees, Woods and Forests: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 乡村地理教授查尔斯.沃金斯(Charles Watkins)写道:“树木和树林的寿命常常超过人,予人秩序、连续和安全的感觉。”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少文化语境里,人们一般是从本土树木,本土树木构成的林地或森林获取这种“秩序、连续和安全”的感觉。所谓杨柳依依,人世无常,但只要祖国白桦林、故乡菩提街,老村古槐树,故居十二棵橡树还在,个人或集体的记忆就有可靠的凭依,失去的时间可以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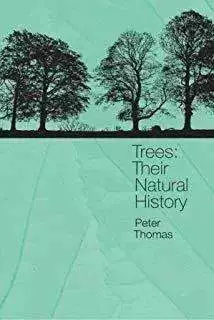
然而,一旦涉及到外来植物,特别是澳桉这种兼具环境“适应性(adaptability)”和入侵性的优势树种,公众的感知会因人(或族群)而异,因时而异,这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有时“几乎深不可测(almost unfathomable,沃金斯语)”。尽管如此,看似歧见丛生的公众感知里,“异”在何处还是清晰可辨:作为经济作物(tree crop)的速生澳桉连片成海,而“成排、成行、整整齐齐的、绿油油的桉树林”正是生态美学家、艺术家甚至公众厌恶的绿色沙漠,毕竟大自然从不拉直线。此外,急功近利的大林场业主和桉农,3-5年就会轮伐一次桉树,留下大片残桩,呈现出惊人恐怖的景象。然而,一旦澳桉树龄超过十年,再与其它林木杂错交织,出现在缓坡、丘陵、水滨,优雅之美流露无遗,它就是植物学家、园艺师、艺术家、文学家为之迷醉的观赏树和风景林。晚清时期服务宜昌、蒙自等地中国海关的爱尔兰植物猎人,奥古斯汀.亨利, 遍阅北美、中国南方奇树异花,就对澳桉的“风致(attractive features)”赞美不已。毫不奇怪,在西方,桉属树种特有的“轮廓”“肌理”“叶型”和“气味”是景观设计师和园艺师特别青睐的“风景元素”。不少大地艺术杰作,如以葡萄园而著称的加州纳帕谷,桉林是当地主要植物群落,叶片微微银光翻飞风中,挥发出的薄荷香味萦绕其间,构成清晰可辨的地景和清新可嗅的气味景观(smellscape)。

Erin-Hanson-Napa-Eucalyptus
所以,1896年开始引入蓝桉(blue gum)的昆明,到了抗战时期,“三人方能合抱的大尤加利树”(沈从文语)随处可见于滇池、翠湖、龙头村、北门坡、唐家花园、金殿后山等处。作为“植物界最高的树”(冯至语),昆明人俗称的“洋草果树”,别名“灰柳树”的蓝桉天然地木秀于林,一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出镜最高的柳树,不仅衬托昆明漾碧环翠的风景气质,而且成为一代学者和作家的诗情哲思的酵素。这一时期流寓边城的北方学者和作家,如康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林徽因等,他们的昆明叙事和抒情与澳桉密切交织,以澳桉审美为中心的书写渐趋一派。通览以尤加利树(或桉树)为主题的咏物诗文、涉及澳桉的游记、日记、通信等散文创作,甚至林学研究论文,笔者发现:不同作者笔下,同一种蓝桉撩起不同强度的情感(从感伤到崇高)和不同文统的联想(从美人到上帝),但依然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特征:仔细地观察澳桉自然特征(physicalfeatures),精确地描摹它的生境和美学效果——笔者将这一特征称之为:对植物学的热情(enthusiasm for botany)。因为这种对植物学的热情,沈从文等人自觉或下意识地成为华兹华斯、约翰.克莱尔、D.H劳伦斯那样的“植物学家诗人(the poet as botanist)”,将求真的植物学与唯美的艺术结合起来。
丰富斑斓的中国植物文学,有很大部分取材于外来植物,如安石榴和印度菩提。晚清来华的澳桉自然也会吸引文人墨客的注意。据笔者考证,第一首有据可查的咏桉诗应该是笔名为“浩”的作者于1935年发表在《外部周刊》上的古体诗《桉樹(Eucalyptus)歌贈筱珍》,状物疏空,意蕴平平,但是林学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诗人推销澳桉的经济价值媲珍“龙脑沉檀”,贵超“椰子槟榔”,是优良的绿化树(“此邦荒壤可为林,种子更求菰米黑”)并点明西湖桉树的来历:“邵子昔年海外归,数株手种西湖侧”。可以说,这首诗相当于韵体的《劝种桉树》。
最早传达植物的实用价值和艺术美且又扣合昆明澳桉的书写应该出自林学家康瀚。1939年,康瀚发表了一篇造林论文《桉树:云南林业之新富源》。他特辟一节“桉树的自然美”专论桉树的景观价值和如画美林景效果:
自昆明城,出小西门,沿大观马路,两旁树木森林,叶茂荫浓,策蹇驰骋,清风徐来,田畴广芜,沟渠萦回,小舟容与,西山在望,往来期间,诚足以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也。此种迷人之风景,虽天然之佳山水,故占首要之位置,而人工点缀之树木,实为之生色不少也。
在两旁翠葱茏之树木中,除昆明习见栽培以护堤之柏木外,有树杂生其间,躯干挺拔,长身玉立,叶条缠长,酷似杨柳,临风婀娜多姿,嫩枝含霜,如敷薄粉,揉叶闻香,味同兰麝,外皮若服罗裳,有健康美,富娬媚姿,仿佛西方美人,此是何树?即本文所欲讨论之桉树。
造林与造园本为姊妹学科,而园林又是贯通诗画的立体艺术。因此,作为林学家的康瀚走笔至此,脱下论文逻辑和论证的紧身衣,转用山水画家游动的目光勾画烽火之外的滇池,一处乱世的大地艺术:远山、中水、近林;又以景观设计师的空间感再现堤岸林地(wood)的尺度、比例和节奏:林木葱茏,柏桉杂生,叶茂荫浓;再以植物画家的严谨敷陈澳桉的生物学特征。一节“桉树的自然美” 与其说这是“隐于”科学论文中的“澳桉赋”,不如说,这是堪与《瓦尔登湖》某些章节对读的自然写作,更是一节植景设计(design with plants)范例介绍:濒水而植,长身玉立的澳桉与盘曲苍虬的中国柏树交相辉映,美在线条对比,色彩互补,层次错落——这一点,恰好是19世纪英国风景园林的一个“秘诀”:将东方植物混交间种于英国本地树丛之中。
在不足250字的“桉赋”里,康瀚遣词造句,无不带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暗记,结句笔锋一转,却将澳桉比喻有健康美的西方美人,留给读者联想的可能。果然,六十年后,云南诗人于坚将这一比喻进一步性别化为性感情人:“哦/贴着那光滑的腹区/我听得见/青色的溪水在黑暗的胴体中流淌/我的赤条条地沐浴在光辉中的女人/……
没有资料证明于坚读过隐于民国旧刊的康文,更没资料证明康文可能影响到另外几位写到桉树的作家。不过,即使他们先后、分别、独立书写,彼此的“共性”还是有迹可循:无论是林学家还是艺术家,都力图使“植物种属的属性(attributes)变成表达的元素”(罗斯金语)。
同样写于1939年,朱自清的《蒙自杂记》记叙远离昆明的蒙自日常风景的高光部分:南湖桉堤,旁证澳桉固堤防风的优点已在云南广被利用。较之康文,朱文细节略逊:“高而直的干子,不差什么也有‘参天’之势,细而长的叶子,象惯于拂水的垂杨”。耐人寻味的是,滇池桉堤令造林专家康瀚想到:天然山水也需人工林点缀;南湖桉堤却让散文家朱自清幽起故园之思:暂把蓝桉认做自辽以来就主导北平植景的柳树。实际上,中国柳树一如澳桉,用途甚广,易栽易生,伐而复萌,千百年来广植于大江南北水边路侧:“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 雍裕之),“ 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杨万里)——这是中国城乡战前寻常植景,而朱自清念兹在兹的北平什刹海,就有“柳堤春晓”名胜,此时已陷日寇之手。笔者认为这才是故园之思的留白。
朱自清状物抒情,素来绵密,但写到桉树,却简笔化之。也许,把澳桉比作国树之一垂杨(柳),自然就需省些笔墨。毕竟,我们的古典文学里存储了太多柳树的意象、象征和神话,一般读者会被联想的惯性拖进经典宝库,此柳彼柳,会心之处俯拾即是。
不过,转入下段,朱自清笔锋一挑,单挑澳桉与建筑的关系。晚清留下来的蒙自海关前,“高大的尤加利”和“软软的绿草”搭配出这个紧邻法国前殖民地边陲小城“浓得化不开”的异国情调,而这异国情调,确言之,就是澳洲风情。熟读麦卡洛《荆棘鸟》的读者应该记得:在干旱燥热的德罗海达牧场府邸前,一排树干浅白高达70英尺的魔鬼桉(ghost gum tree),遮住了楼房,挡住无情的阳光,而蒙自干热气候也特别适合并需要长于遮阴的澳桉。19世纪末期,设计小城寥寥可数的公共建筑(海关、领事馆、火车站等)和公共空间(南湖公园)的人一定充分考虑了澳桉的实用美学价值。
略使笔者遗憾的是,朱自清在小而美的蒙自借居五个月,熟悉并欣赏它的日常“静味”,却没前瞻性地意识到:远离战火的蒙自风景“绝非意味着稳定和传统,而是人类过去的漫游和交换的生物学记录”
他写进《蒙自杂记》里的“澳桉”“芒果”“叶子花”(甚至木瓜),没写的蒙自名产石榴、番石榴、柠檬、红薯都是外来植物,或者外来的改良品种,如越南木瓜。
真能与康瀚一较专精的要算沈从文。自幼生活在以植被多样性著称的湘西山地,一如英国乡村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1793-1864),沈从文无师自通地积累了丰富的植物学知识——他的虎耳草已如华兹华兹黄水仙成为著名的文学植物。他自谦认识的“几十种树木”就包括昆明澳桉。也是写于1939年,沈从文的《昆明冬景》开首就锁定澳桉常青的生物特征,而这一特征更加突出昆明四季如春的物候:
新居移上了高处,名叫北门坡,从小晒台上可望见北门门楼上用虞世南体写的“望京楼”的匾额。上面常有武装同志向下望,过路人马多,可减去不少寂寞。住屋前面是个大敞坪,敞坪一角有杂树一林。尤加利树瘦而长,翠色带银的叶子,在微风中荡摇,如一面一面丝绸旗帜,被某种力量裹成一束,想展开,无形中受着某种束缚,无从展开。
沈从文一定仔细地观察过澳桉树叶革质蜡光和摇动的姿态,印象深刻,以至于九年之后,在《怀昆明》(1946)一文中,他继续写到:“院子是个小小土坪,点缀有三人方能合抱的大尤加利树两株,二十丈高摇摇树身,细小叶片在微风中绿浪翻银……”, 从蔡锷故居萧条和同街唐家花园“美轮美色”的鲜明对比伸及推翻帝制的历史和两位护国英雄的命运。
如前所说,桉属一大景观元素在于它的叶态(foliage),蓝桉就被列为优良观叶植物。历史悠久的北门街有两处名人住宅,蔡锷旧居和唐继尧府邸都植有蓝桉,先后分别进入沈从文和林徽因的书写。凑巧的是,沈从文是在1938年初抵昆明租住蔡锷旧居,“老式的一楼一底”(沈从文语),林徽因则是在1946年重返昆明客居唐家花园,昆明最大的私家园林。两处蓝桉都有些年头,风姿足观。特别是西式风格的唐园,澳桉、日本樱花、云南茶花、兰菊等等混交间种的花境更是冠绝西南诸省。更凑巧的是,作为林徽因沙龙常客又有文字图绘天赋的沈从文和林徽因的赏桉趣味相当靠近。不同于康、朱(他们的澳桉描写兼顾它的生境、混交桉林的美感和实用效果,沈、林则侧重孤桉的细部特征和神韵——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受到西方18、19世纪以孤树为表现对象的风景画影响。
来看林徽因“图绘”给汉学家费慰梅的唐园澳桉:“……这房间宽敞、窗户很大。使它有一种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甚至午后的阳光也像是听从他的安排,幻觉般地让窗外摇曳的桉树枝桠把它们缓缓移动的影子映洒在天花板上!”
建筑师林徽因也是室内设计高手。罹患肺结核,静卧养病的她一定长久地观察着天花板上桉树枝桠的光影变化。无论是沈从文发现的“翠色带银”还是林徽因迷醉的“幻觉般……缓缓移动的影子”,都指向观叶植物桉树神秘的特质。云南高亮度的亚热带阳光就像舞台设计师克雷擅长控制的灯光,把桉枝的半透明、飘忽、似有若无展现得介乎于实存与幻影之间。参看书信原文:“splashes of faint moving shadows”,似译“虚影浮动溅光”更佳。根据笔者对林徽因装饰趣味的观察,她是一个没来及达成(achieved)现代主义装置艺术家。
至此,笔者可以总结:以上四位的澳桉描写,各有植物学侧重,也各怀桉外之意:康瀚的田园牧歌,朱自清的故园之思,沈从文的历史观察和林徽因的虚灵(illusive)美学。然而,真正将澳桉升华到宗教地位,且与西方神话中“世界之树”产生呼应的则是冯至的《尤加利树》:
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
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
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
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
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
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
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
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
冯至的这首十四行诗,历来多有方家各抒己见,现有成果甚至可以单列出冯至研究的一个分支。笔者认为,还有新的空间潜藏在宗教植物学和德国植物哲学交叠之处留待“启封”。最重要的是:作为外来植物的澳桉,先于它巨大的经济价值实现之前,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美的一笔财富。
五 不是结语的结语
在《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的绪论里,曼恩交待他读到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突兀起句给予他的方法论启发。紧随其后,曼恩一路追踪包括动物在内的新旧世界物种如何随欧洲殖民者足迹而传播扩张到地球最偏僻的角落,并连动一系列环境后效和文化反应。同样地,受曼恩启发,尤其是他的点题之句“我的花园里有世界各地的植物,……”的启发,我开始以全球植物交换史的眼光细察桉树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注意到当代云南诗人于坚和浙江诗人李浔笔下的桉树。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两人的桉树书写发生于生态争议漩涡时期,公众的生态焦虑却像桉树皮一样自动从他们的文本脱落。笔者不由得思考个人创作是不是必然地与新历史学家强调的“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发生意识形态交换?研究过程中聚拢的文献牵引我思考到更大问题,比如,进入中国120年的澳桉,为什么只在生态利弊争议话语体系里起伏,或止步于《中国桉树》(祁述雄著)这种专业而孤立的技术总结里,却从未进入中国环境史、社会文化史学家的视野,像人类学家敏茨(Mintz)的“土豆”,史学家贝克特(Beckert)的“棉花”,显露出历史主演之一的浩大的文化影响?凡此种种,值得笔者继续追踪下去。
我们尊重原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谢谢!
(责任编辑:冯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