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冯尔康,历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1934年生于江苏仪征,195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曾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概论》《清代人物三十题》《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等。

(2013年,冯尔康在“传统中国社会与明清时代”学术研讨会上)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度兴起。冯尔康教授是中国社会史复兴潮流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其社会史研究既有《中国社会史概论》的理论总结,也有宗族史、谱牒学、日常生活史的精深探研。在新时期,如何将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前推进,冯尔康教授对此有着深入的思考。
对宗族史的贯通研究
问:冯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您从事史学研究数十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治学精力,不断有新著问世。这次想请您谈谈近年主要关注的问题。
答: 我想这将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交谈。说到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先前中国社会史研讨的继续,也有一点领域的扩展。主要精力用在宗族史方面,对研治清代宗族史和中国宗族通史用力最勤。此外适当进行了女性史、海外华人史的研习。清代天主教史原先基本没有接触,近年投入不少精力。总之,我基本上还是围绕社会史做文章。
问:我们是不是先从宗族史谈起?“五四”以来很长时间,宗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遭到取缔。您是怎么开始关注到宗族史这个研究领域的?
答:以前,包括我在内的激进力量、激进学人对宗族的态度是全面否定的。主流意识把族权作为封建主义“四权”之一予以批判,斥责它对族人的控制、迫害,是土地革命的对象。我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接触宗族史的,其时我撰写清代租佃关系史研究生毕业论文,阅读地方志、学术笔记、家谱、文集和政书。我受的训练是,每读一本书要全面搜集资料,不是只找与目前研究课题有关的材料。这样我在租佃关系史之外,获得不少宗族史资料,很有兴趣,认为值得研讨。这时,社会上兴起天天讲阶级斗争热潮,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而封建主义回潮就是农村有人修家谱。我当时本着史学研究为政治服务的要求,觉得应该参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这是我宗族史研习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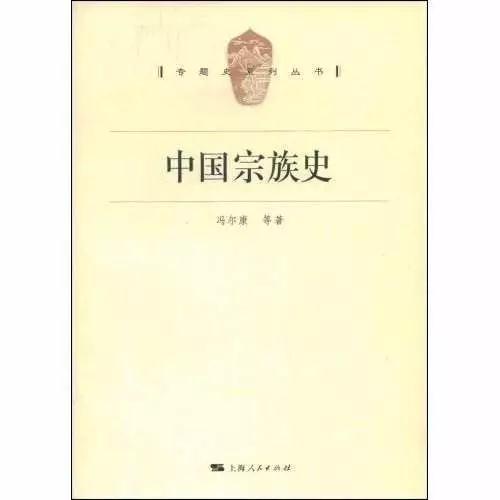
问:后来您将宗族研究深入下去,做出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请问在研究中,您有哪些认识?
答:我想先说说用力最多的清代宗族史。这方面,我发表了30多篇专题论文和心得笔记。其中既有专论某一具体方面的,也有综论清代宗族特征的。
通过对清代宗族的族长、祖坟、祭礼、族谱等一些具体问题的考察,我对清代宗族情况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较为明确的认识,对此前的宗族批判论作了深刻反思。比如相当一段时间内,宗族族长被看作宗法专制体现者,是欺压族人的恶人。但是我发现,这种看法失之偏颇。在清代,族长及其助手的产生常常不是通过宗子制继承的,而要经过族中部分人的协商遴选。族长行使权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要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要受到族人“合议”的制约。出现问题,族长甚至会被免职。为了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宗族常常会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并要求他振兴族务、遵守国法、做到自律。当然,由于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有专制因素,甚至有的族长作恶多端。但把他们都视为“青面獠牙”,就并非清代宗族族长的实况了。
清代宗族是含有宗法成分的自治性互助团体。宗族确实含有宗法因素,但不应过分夸大。其自治、互助的功能,适应了民众生存生活的需要,起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另外,清代宗族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中介组织,促使贫乏的社区生活面貌有所改变,有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应给予肯定和尊重。宗族文化中的互助精神、自治意识、亲情意识是中华精神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建设当代社会文明的有益资源。
问:我觉得您的评价是客观的。从清代宗族的研究出发,您对宗族通史也作了富有建设性的研究。就我所知,您近年不断有新著问世。下面,能否讲一讲您的中国宗族通史研究?
答:好的。我对从商周至21世纪初年的宗族、宗亲活动作了分析,将宗族史分为5个阶段。先秦为贵族宗族阶段,秦汉至隋唐为世族、士族宗族阶段,宋元为官僚宗族阶段,明清为绅衿与平民宗族阶段。20世纪以来是第五个阶段,宗族史开始进入宗亲会阶段,颇具俱乐部性质,完全克服了传统的宗法性。其实宗亲会时代,“宗族”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族了。
在宗族通史研讨中,我还梳理出中国宗族的4个特点。第一是具有持久性。宗族持续发展,可以说是唯一从古至今始终存在的合法社会团体。其他团体,比如合法宗教、行会,都不如它的历史悠久。第二是民众性。宗族将广大民众组织在它的团体之内。明清以后,宗族逐渐民间化、大众化,成员众多,结构也变得较为复杂,能够将广大的民众吸纳进去,成为了民间最具广泛性的团体。第三,宗族是具有某种自治性质的团体。第四,宗族是中国君主专制的基础,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影响着民间社会生活。最主要的是,历朝政府大多实行“以孝治天下”方针,希望用“孝”、用宗族来稳定其政权。
问:谈到宗族与国家关系,您认为研究宗族史与研究中国历史是怎样的关系呢?
答: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族史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从组织形态上,国家的君主制和宗族的族长制性质是相同的,可以说,从上到下,家长制一以贯之。在很长时期内,国家、宗族的宗法等级性是一致的,社会的等级构成是“皇帝-贵族-官僚-士人-平民-贱民”,宗族的结构式是“皇族-贵族宗族-缙绅宗族-衿士宗族-平民宗族”。宗族形态与社会性质也是同步演进的。在古代君主制社会,宗族组织形式是族长制。近现代转型期社会出现了族会暨议长制。现代社会则产生了宗亲会会员大会暨监事会制。在君主专制社会,没有民主,民权极其微弱,极难建立各类团体,也没有政党,然而宗族始终是合法的。宗族一方面是政府的附庸,但另一方面也有其自治性。宗族是实行民主制的一种社会背景,也可以说是社会基础,是今日村民自治的前奏。基于此,我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可以从研究宗族史入手。当然,从宗族史看中国史只是一种方法、一个角度,不会也不可能排斥其他研究法。
跨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体悟
问:近年来,您将天主教传教士在清代的活动、清朝诸帝对天主教的政策,特别是康熙帝与传教士的互动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为什么选择这个专题?
答:我是研究清史的,清代天主教史自然也包括在内,但不是必须要进行的内容。我作此项研究有契机、机缘、学术上“知耻”诸种因素。
契机是2011年10月到2012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交流大展”。其间,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联合举行了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出席并写了论文。会间参观“大展”,我第一次见到康熙帝模仿、创新制造与使用的数学仪器,有圆规、角尺、十二位盘式手摇计算机、几何体比例规、八位对数表等。以前,我从文献中知道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些情形,但文献记载平平淡淡。这次欣赏到实物,令我大为震撼。中华帝国一向以自己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康熙帝却屈尊以西洋传教士为师,并模仿制造西方仪器。这令我真切感受到他尊重科学新知识的意识和强烈的求知欲望!震惊刺激我去了解“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历史,而康熙帝的西方知识是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研习这个课题,就自然涉及清代前期天主教史。
促进我进行写作的,还有“知耻”的思想因素。在与友人王思治教授合著的《康熙事典》中,我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将罗马教廷传信部的马国贤当作了耶稣会士。发现后,我心情非常沉重。我是以实证史学观念治史的人,竟然出明显的史实差错,还配为史学工作者吗?对康熙帝尊重科技的佩服与对自己差错的惭愧两相结合,于是有了研治康熙帝与西学、康熙帝与传教士关系史的写作冲动和决心。

(康熙用过的绘图仪器)
问:从2011年到现在5年多时间,您发表了十来篇关于清代天主教史和传教士的文章。听说最近还要结集出版(按:现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您能谈谈在这项研究中有何心得吗?
答:在清代天主教史的研究中,我着眼于政治与宗教的双向关系,既要明了天主教发展变化史,又从教会史角度观察清朝的政治。要说心得,我有这样几点。一是中庸方针政策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稳定。康熙帝在宽容教令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对笃信儒家道德伦理的臣民与天主教徒均持认可、保护的态度。因此天主教虽与“儒教”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并没有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二是君统与道统分离是古人的政治智慧。在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上,许多臣民和皇帝政策见解不同。历史证明,君统、道统的分离对社会有好处。三是应该正确对待外国文化、先进文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文明从未间断,这令中国人产生根深蒂固的世界中心论,蔑视外国文明。但是这种中心论的实质是帝王中心论、统治者中心论,是统治者需要的观念。在这种情形下,康熙帝能够承认西方文化,主动招募西方科学技术艺术人才,其博大襟怀,超越其他帝王。但是,他又是“中体西用”论的提倡者。他不懂得世界文明中有普世性的进步成分,只知维护“道”不变,这就限制了他的政治眼光,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问:海外华人社会史也是您近年的一个研究课题。传教士来华与华人海外移民可以说是一组相互呼应的题目。通过考察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一定会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吧?
答:我对海外华人历史的关注,起初是宗族史研究的延伸。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出席了几次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些会上,我从与会的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学者那里获得了海外华人宗亲会的一些知识,并得到了港台地区有关出版品,这让我大开眼界。这些知识对我的宗族史研究很有启发。后来,在我写《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宗族社会》等书时,将海外华人宗亲会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近些年,我经常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旅行中也在不断搜集华人史资料。
我对海外华人的中华礼仪活动进行了一些观察,感到这些活动给予了他们精神寄托与慰藉,反映出海外华人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在进行这些观察时,我的脑际萦绕着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挥之不去。“野”是相对中心而言的,也可以包括有传统文化联系的邻国、有华人的国度。礼的某些内容在中心地带消失,在“野”则可能保留着。中心地带失去的礼,有的已经不适合于现代社会,理所应当让它消失。有的则未必,或一时消退,而后又被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重新拾回来。现在我们就是要认识那些需要拣回来的东西,让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我有点惭愧,这方面深入探讨还不够,但是也在跟踪调查新资料。
纵横结合思考社会形态问题
问:可以看出,您的研究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但在一个个问题后面,似乎有着对历史进行宏观把握的目标。是不是这样?
答:是这样的。我的史学研讨内容,主要是具体史事,具体的人物、制度和事件,但是微观研究中确实有着宏观的旨趣。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而且是强烈的意识。我的方法是讲求“纵通”与“横通”的结合。“纵通”是注意研究对象的古今发展线索,“横通”是留心研究客体与其他事物彼此间的关联。我希望用纵横结合的方法达到对具体历史有较大范围的理解和说明。
问:能举例说明您在研究中的宏观思考,以及“纵通”“横通”方法的运用吗?
答:好的,现在我来说一些事例。前面说到我从许多微观考察中梳理出宗族史发展的5个阶段,我想这可以算是“纵通”的一个例子。“横通”的一项成果是从宗族史探讨拟制血亲史及双方关联,撰写了长文《拟制血亲与宗族》。历史上存在着不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在社会交往中比附血亲关系。我使用人类学“拟制血亲”概念,来描述这种历史现象。认同宗、拜干亲、结拜金兰、收养义子、奴从主姓、皇帝赐姓等,都属于拟制血亲或类似拟制血亲,以此同宗族发生了联系。透过这些历史现象,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社会乃至近现代社会的一个侧面,从而加深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的演进,古人社交关系和社交生活,历史上的移民社会及移民生活等。
“纵通”与“横通”结合的一个例子,是我将宗族史与社会形态史的研究融汇在一起。社会形态问题是研究历史学绕不过去的问题,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学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封建宗法社会”。我对此提出质疑,提出秦汉以降为“变异型宗法社会”。这是基于3个事实。其一,秦汉以降的帝制具有浓厚的“家天下”成分。皇帝和皇族制度仍然是宗法专制制度,但天子不再身兼宗子,变为单纯的国家元首。其二,实行小宗法制。随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皇帝的大宗地位已无诸侯小宗可以支配、维系。民间宗族壮大,到古代社会晚期,宗族成了民间化、大众化的组织。其三,宗法专制性、族人依附性既得到保存又受到削弱。宗法性与专制性是相伴而生的。宗法的血缘关系与社会等级制及观念结合,成为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基础。不过宗族民间化之后,族长与嫡长制逐渐脱离关系,通常由有力者出任,出现遴选制、推举制。宗族对族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这是历史趋势。基于这3个事实,我提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说法,我不愿再继续沿用。
问:在您和学界同仁的努力下,如今社会史已成为一门显学。可以说由于这一领域的异军突起,史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史是一门具有深刻现实关怀、通古今之变的学问,在您看来,继续深化与拓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努力方向有哪些?您对未来的社会史研究有哪些希望?
答: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继续深化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不停地拓宽研究领域。我们处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研究方向,最大的问题当然是人类社会走向。人类的追求与生活是怎样的?人类未来将是怎样的?这类宏观问题需要时刻徘徊于脑际,就我目前认识到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有3个。
一是应特别关注以人为本的历史。要尊重社会个体———“人”的历史。研究人的生命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生存环境史与生态环境史,即政治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经济生产、社会风俗。研究身体史,包含卫生医疗史、生育史、死亡史。
二是应研究社会细胞———家庭的演变史。学者吴小英近日提出,我国有着从“去家庭化”到“家庭化”的变化。我知道,在“家庭化”趋势下,家族会、宗亲会、修谱活动频频出现,不仅修纸质本的家谱、族谱(宗亲谱),还创造了网上修谱。在现代化过程中,宗亲活动没有消失或沉寂,这就向宗族史、家庭史研究者提出研讨的新课题。
三是应关注第三产业大发展形势下人的活动史。随着社会富裕、生活平静而有保障,体能锻炼、刺激性娱乐和探险应运而生。如体能活动大量减少,为活动身体,家庭购置跑步机,社会出现健身房行业。攀岩、悬崖跳水、蹦极活动增加。体育明星、演艺明星的被追捧,实质是被消费。休闲式旅游业,连同餐饮业大发展,成为某些国家、地方支柱产业,等等。
当代社会新现象,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与古代、近代社会有着内在的历史渊源,也是未来社会发展演变的依据,从当下社会现象回观历史,是纵通地观察历史,可能认识得准确一些。
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我的愿望是,大家都来关注下面说的两个问题。社会史研究成为“显学”,不一定完全是好事,容易难以为继,容易失去真理,所以我一再呼吁要警惕。同时还要警惕研究的碎片化,牢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为写出整体史而努力。


